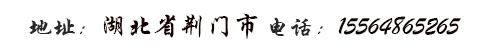山茶花情系故乡的棕树民族时报
| 中科白癜疯医院是骗人的吗 http://www.wzqsyl.com/老家所在的村庄叫徐家村,坐落在临沧市云县涌宝镇北面的大山深处。我年少时,村庄周围贫瘠的耕地里到处都有棕树。棕树根系发达,稳固性强,能防止耕地坍塌,所以大都栽在坎头上。几乎有一道坎,就有一排棕树。它们大都高达两三丈,干笔直无枝,叶大而圆,似扇似轮。“棕树棕树,一根圆柱。天天向上,干劲十足。片片阔叶伸巨掌,高把蓝天来托住。腰直腿硬脚跟稳,笑看杨柳随风舞。”临沧籍云南现代著名教育家、诗人刘御先生的这首《棕树谣》是故乡棕树的生动写照。棕树是故乡亮丽的风景!它们像一排排整齐的、身姿挺拔的士兵守护着故乡的土地,守护着生我养我的村庄,为故乡、为村庄平添了许多诗情画意。夜晚,微风吹过,棕树那巨扇似的阔叶相互碰撞、拍打,会发出“啪啦啪啦”的声响,像海浪轻涌,像腰鼓轻擂,像马蹄践石。不知有多少个繁星高悬、月色朦胧的夜晚,那“啪啦啪啦”的声响如小夜曲一般把我送入梦乡。谚语云:“一千棕不怕家内空,一千桐一生不受穷。”四十几年前,对于故乡人而言,棕树是宝树——浑身都是宝!它的干可以用来烧火做饭,可以用来铺路搭桥,可以用来建房盖屋,还可以凿成槽,把山泉水引进家家户户。它的叶可以做成扫把用来扫地除尘,还可以用来捆绑东西,农村里的烟叶呀,豆子呀,青菜秧白菜秧呀,都是用棕叶捆绑着拿到集市上去卖的。它的花可以充饥。在那粮食奇缺的年代,每年农历一、二月,人们常把尚未开放的棕花(俗称棕苞)砍回家用手掰碎,然后放到锅里煮煮,再捞出来晒干,磨成面,掺在玉米面里当饭吃。当然,那饭并不爽口。它的果晒干后可以拿去卖给收购站,挣几元或几角买盐巴、布头、肥皂的钱。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收购站曾大量收购棕果,每市斤四五角钱。有人说收去的棕果出口国外,真假不得而知。棕皮更是棕树的宝中之宝。棕皮晒干后卖给收购站,价格比棕果高一两倍——它是山区农民的重要经济来源。关于棕皮,我还有一段刻骨铭心的记忆。我在涌宝中学上初三那年,每个月的伙食费是七元二角。父亲一般在上个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天给我下个月的伙食费。有一个月,到了该给我伙食费的日子了,家里却连一元钱也拿不出来。父亲去向邻居借,连续借了好几家,别说七元,连一元都没借到。大概到了下午四五点钟,父亲眉头一皱,忽然想到了我家“自留地”里的那十来棵棕树,想到了棕皮。他立刻让我带上刀子、绳索和他一起去剥棕皮。到了地里,他爬上树去剥,我在树下割棕板(叶柄根部和棕皮连在一起的比较坚硬的部分,长一尺左右,宽两寸左右)。比较高的棕树,需在距离顶端五六尺地方横着绑上一根结实的木棍,然后人分开双脚站在木棍上才能剥。当剥到第八棵棕树的时候,剥着剥着,绑木棍的绳索突然断了,父亲重重地砸在树下的棕叶堆上。万幸的是,父亲是双手死劲抱着棕树的干往下滑了一段后才坠落到地上的,加之下面有许多棕叶垫着,所以没有造成重伤,只是手臂和肚皮都擦破了,血淋淋的。当晚,父亲和我一起坐在火塘边用火烘烤棕皮。烘烤的过程中,他只和我讲过三句话:“注意翻着,别让火烧着”,“再困难也要好好地读书”,“明天早上把棕皮拿去卖给收购站”。三句话是分开说的,前后两句之间间隔的时间很长,没有开头,没有下文。烘烤完四五十片棕皮已是后半夜了。第二天一早,我用棕叶把棕皮捆成一捆扛去卖给了收购站。我至今还清清楚楚地记得卖得八元四角五分钱,买了一个月的饭票,还剩一元多。星期六回家,我把剩下的钱一分不少地交给了父亲。时光流逝,沧海桑田。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故乡的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乡亲们的日子越过越红火,吃穿用住早已不需要依赖棕树了。棕树不再是宝树,它变得可有可无了。然而,我希望它永远屹立在故乡的土地上,永远充满生机,让它时刻提醒我们珍惜改革开放的成果,珍惜今天的幸福生活,并努力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作者:徐家永,单位系云县第一完全中学)转载请注明来源《民族时报》 |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xiangjiapia.com/xjpjd/11294.html
- 上一篇文章: 新英雄6月9日四转资料片登临玄境飞
- 下一篇文章: 面粉这样做,比馒头好吃,比包子简单,蒸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