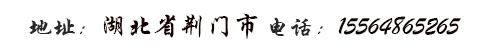父亲冒效鲁与傅雷的友谊冒怀科
|
最近看到网上媒体传播由大剧院零距离对傅雷之子傅聪珍贵的访谈,把我的思绪又带回到青年、中年时期。 年我陪着年迈的父亲到龙华殡仪馆参加傅雷夫妇的追悼会,傅聪为料理父母后事专程回国。在去往龙华的路上父亲不言不语,心情沉重。当我们父女走进庄严肃穆而又俭朴的大厅门口,傅聪、傅敏两弟兄迎面向父亲亲切而紧紧握手,久久没有放下,亲切又伤感地叫着冒伯伯、冒伯伯。父亲过去是他们家的常客,傅聪的琴声伴随着两位学人的谈笑风生,一位豪情满怀,一位严谨耿直…… 父亲和傅雷是在年由钱锺书介绍相识,那时傅雷夫妇第一次去北京(当时还叫北平),正好父亲也在,就义不容辞当了他们的向导。父亲陪他们逛东安市场、王府井大街、古玩铺、北海公园等。父亲出生北京,十多岁时在北京念书,骑自行车穿行南北大街小巷。年父亲回到上海后,傅雷在淮海路巴黎新村设宴款待父亲。 年傅雷迁新居江苏路寓所,一天电话相约父亲上门做客,傅雷拿出钟楼牌特制五加皮款待父亲。父亲虽然从不喝药酒,但这五加皮味道醇厚,父亲说:中国自古以来有把人比酒的习惯,傅雷的为人犹如他所珍藏的佳酿——五加皮。我小弟怀康告诉我:“我很小五六岁时,爸爸常带着我,晚上坐三轮车到傅雷家,他们两人聊到很晚,兴致很高,我往往瞌睡,经常带着睡意坐三轮车回家,经过静安寺看到有个钟……” 新中国成立后,俄语人才奇缺,为此不少学校争先恐后请父亲去教书,傅雷推荐父亲到光华去任教,胡绳通过沈志远聘请父亲赴北京编译局工作,但父亲选择了由陈毅市长介绍到复旦任教。陈毅早在苏北抗战时,已从同窗王统照那里了解到父亲的一切情况,中外文都好。父亲首选了复旦外语系就职。 父亲到复旦教书后,每天晚上要为新文艺出版社校对苏联的美学、文艺等大量俄文书籍。出版社的俄文编辑戴际安常去模范村送稿,文稿也催逼得紧。戴后来成为译文出版社的著名编辑,我进译文后成了同仁,戴大编还津津乐道追忆约稿父亲出手快的情景……父亲初上手就要他翻瓦卓夫的短篇小说,父亲嫌自己文笔笨拙,文白杂糅,请傅雷审阅。傅雷在父亲的译文上用红钢笔密密麻麻地加以润色和修改,有意思的是在日后他问父亲的朋友,为什么冒效鲁不见怪……说父亲那么有雅量!父亲也常说为人校稿有涤垢衣之癖(语本伏尔泰)。父亲生前再三教导我们儿女:“学问、学问,要学要问!与人要公平竞赛。”我在翻译苏联作品《佐尔格传》(又名《同第三帝国斗争》)遇到一些难译地名、句子请教父亲,他都一一答复,有的他也查考辞典和资料。我常听到父亲在模范村二楼门外电话,与老白俄、师友的交流中的口头禅“何以见得?”同俄国朋友聊得时间最长,推敲译稿文字……年5月24日父亲给我写了四张纸的长信,其中有一段:“人要增长见识,外出多去跑跑。跑一趟南通,多少知道冒家的事,去桂林领略一下甲天下的山水,温习一下柳宗元的记游小品,对文学修养开阔胸襟大有好处。待在斗室靠翻书(字典)是搞不好也成不了学问家的。钱伯伯夫妇都是在外国东奔西跑,结交名流饱览名胜,所以加上翻(看)书,勤于记笔记,就成了大学问家、大小说家。” 傅雷把他翻译的巴尔扎克小说源源赠送父亲,如《高老头》《欧也尼·葛朗台》《贝姨》《邦斯舅舅》等,以及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贝多芬传》,还有早期翻译的《米开朗琪罗传》《托尔斯泰传》等。他们的交往更多是交流翻译的体会和趣闻轶事。父亲常说:傅雷的过人之处在于他措辞适当贴切,有时甚至颇为奇巧,可谓神来之笔!父亲佩服傅雷的大胆创新,他的译本称国王为“王上”是他“独家首创”。傅雷是上海浦东人,为了使译文通俗,他反复琢磨老舍的地道京白,参考一些国语词典。对书中一些细节、人物背景也绝不放松,为了解决疑团,他不惜写信向万里之外的异邦友人和原作者罗曼·罗兰询问,把上海书库和徐家汇藏书楼的法文参考书查遍,务必做到合情合理,正确无疑后才罢休。父亲说傅雷的译文也仿照白居易“老妪能解”的办法,往往把译稿念给住在他二楼的宋老奶奶(宋梯芬妈妈)听听,有什么扞格难通、疙里疙瘩的地方。如有,就一遍一遍修改。这种严谨而一丝不苟的态度,让父亲佩服不已!傅雷搜集年前后翻译小说存在的毛病写了万言书寄主管文化部门的领导,被某领导称赏,传令文教翻译界暑天挥汗学习讨论,弄得怨声载道。万言书后引起一场风波,父亲和傅雷开玩笑说:你的大号(字怒安)要改三分之一,把“又”字改为“口”字,“怒”变成“恕”字。 年父亲来上海与儿女团聚,当他偶然走到江苏路傅雷故居前的马路人行道上,“不禁油然黯然地有惘惘凄恻之感。面对灰白墙壁上血红的残阳斑点,成片衬托出黄昏黯淡的色调,往事如烟飏空而降,掠过蒙蒙的尘雾,有时夹杂着雨丝风片,拍打在我的脸颊上,使我猛地想起这位直谅多闻的诤友”。父亲在参加傅雷追悼会后曾怆然作诗缅怀故友: 愁听邻家笛,空嗟鸷鸟亡, 低徊谈笑处,门外立斜阳。 年9月25日 点击“阅读原文”可在文汇出版社微店购买 笔会文粹《这无畏的行旅》 沈芸:余所亚的一封信 周立民:他们在笑什么 陈建华:生命定格在美好的瞬间 张斯琦:敬悼谭元寿先生 胡晓明:千帆渺杳水云期 徐建融:杏坛的“杏”,是杏花还是银杏? 黄开发:师生“称兄道弟”那些事儿 舒飞廉:次第鸡鸣 姚以萍:柴火妞斯巴克 李皖:姜昕和她的《岁月如歌》 卫建民:剪报是我的瑜伽 郑宪:千吨机 曾以约:我在印度坐火车 孟晖:猫粉陆游的重阳糕 预览时标签不可点收录于话题#个上一篇下一篇 |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xiangjiapia.com/xjpcf/6496.html
- 上一篇文章: 芭蕉的功效与作用芭蕉的食用禁忌
- 下一篇文章: 没有了